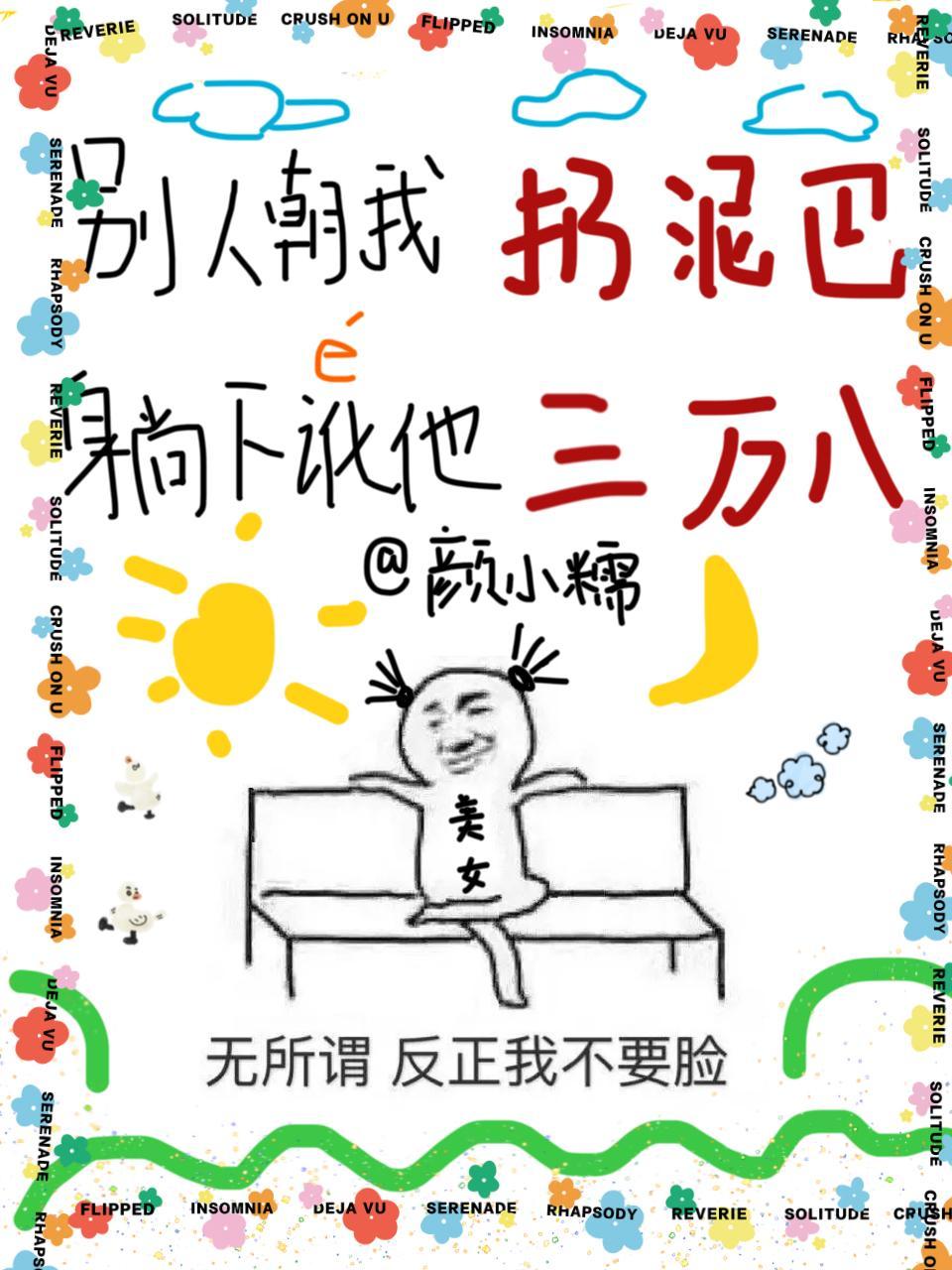燃文书库>李煜乌夜啼剪不断理还乱 > 第155页(第1页)
第155页(第1页)
马天龙活泛起来了,眼睛里射出了光芒:&ldo;不打,日本人会把我抓起来,就像抓聂人雄那样;打,又要人命!你说我怎么办?没办法,拖得一时算一时!&rdo;沈嘉礼看了他这副模样,忍不住笑了:&ldo;没办法没办法,真是没办法。&rdo;马天龙说起话来东一句西一句的,没个章法,上一段还在讲述战场严酷,听了沈嘉礼的评价,他却又忽然转而问到:&ldo;过两天,我去北戴河,你去不去?&rdo;沈嘉礼一愣:&ldo;我去北戴河干什么?&rdo;&ldo;散散心嘛!&rdo;马天龙很诚恳的看着他:&ldo;去吧,好不好?&rdo;沈嘉礼笑了,没说话。马天龙愿意来和沈嘉礼亲近亲近。沈嘉礼其实并不是他的知音,他只是喜欢看到沈嘉礼。这几年里,世事变化太快,他乘风破浪的鬼混到如今,明显的感到了力不从心。而沈嘉礼,从战前到如今,似乎一直都是那个样子。马天龙认为自己应该在沈嘉礼的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。他是个粗鲁暴躁而唯利是图的人,这些年来结识了无数朋友,又与无数朋友闹翻。唯有沈嘉礼像颗星星似的悬挂在遥远天边,不冷不热,总在那里。&ldo;你怎么不爱玩儿呢?&rdo;他几乎是央求沈嘉礼了:&ldo;跟我去吧!坐火车,很快的。北戴河好,不热,还有海。咱们去吃点喝点,住两天,不是比什么都强?&rdo;沈嘉礼仍然是不肯答复,因为知道段慕仁一定不准自己出远门‐‐偏在此时,电话铃响了。电话是段慕仁的秘书打过来的,开篇就道:&ldo;沈先生,请您准备一下行装。委员长明天要去北戴河避暑,要您也随行。&rdo;沈嘉礼吃了一惊‐‐段慕仁向来是死守北平大本营,连天津都少去的。他没从秘书那里问出原因;而放下电话回到马天龙面前,他越发是左右为难,不知如何答复才好了。苟合沈嘉礼对马天龙实话实说,表示自己的确是要去北戴河,不过是与段慕仁同路。马天龙听了这话,心里不大高兴,然而也没有发作,只是嘟嘟囔囔的说出一些不甚中听的怪话,认为沈嘉礼不够意思。在看过沈嘉礼的胖儿子过后,他留下吃了一顿午饭,又吃了一顿晚饭,晚饭时喝了酒,醉了,倒头便睡,睡醒后嚷着干渴,又喝茶又喝汤,顺便吃了顿夜宵。沈嘉礼在家中清静惯了,没料到马天龙会赖着不走,几次三番的心乱如麻,恨不能将其轰出去。马天龙吃过夜宵,神清气爽,腆着一张脸嘻嘻乱笑,又凑到沈嘉礼身边,动手动脚:&ldo;老弟,大半夜的,你怎么还不睡?&rdo;沈嘉礼盯着马天龙那张粗糙面孔,觉着这人本质上虽然不丑,然而平添了这样一道疤痕,真是越看越难看。但话说回来,他难看归难看,可毕竟是个正值壮年的汉子,敞怀挽袖的露出一身腱子肉,堪称是威武雄壮。沈嘉礼和段慕仁鬼混久了,眼中看的、手上摸的尽是臃肿身体、松弛皮肤,厌烦的了不得;相形之下,马天龙倒也显出了几分男性魅力。要笑不笑的翘起嘴角,他心中一动,语气也随之活络起来:&ldo;我睡了,你怎么办?&rdo;马天龙笑道:&ldo;一起睡呗!&rdo;沈嘉礼的目光扫过马天龙的胸膛,脸上的笑容加深扩大了:&ldo;不怕擦枪走火?&rdo;这话让他说的无比暧昧,让马天龙脊梁一麻,心里痒酥酥的舒服:&ldo;擦枪走火怕什么?你还信不过我的本事吗?&rdo;沈嘉礼,手忙脚乱的,和马天龙苟合了一场。他其实并没有强烈的欲望,纯粹是为了苟合而苟合。常年的陪伴着段慕仁,这让他感觉是委屈了自己。马天龙千不好万不好,至少是个结结实实的中年男子‐‐这也就够了。躲在未曾开灯的卧室里,两人都只是退下了裤子而已。沈嘉礼趴在床上,因为是偷欢,所以也别有一种激动的心情。他没想到马天龙居然还很温柔。他的本意只是想被人干一次,干完就算了。可马天龙一旦温柔起来,他因为出乎意料,所以竟是招架不住。身下的床忽然变得柔软起伏,他昏昏沉沉的随波逐流。裤子是在不知不觉间被踢掉了,上衣却是不知何时也没了踪影。恍惚中他仿佛是换了好几个姿势,照例是很安静,气息随着对方的动作而急促或者绵长。到了最后关头,他猛然伸手抓住床单,身体紧绷着抽搐了两下,同时发出了一声低低的呻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