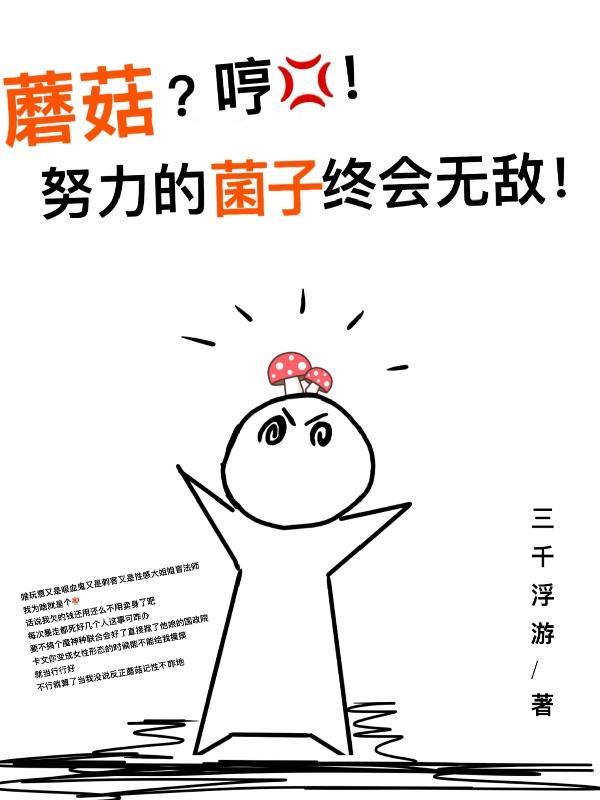燃文书库>梅花洞书 > 第143章 纸切遁身花氏逃出蒲池村 蜾赢负子雄风潜回亓家窝(第1页)
第143章 纸切遁身花氏逃出蒲池村 蜾赢负子雄风潜回亓家窝(第1页)
上回书讲到,鼠长虫带领骁禽郎进入了珞元夕的家,可能是珞元夕的老爹珞崇宣一生作孽太多,以至于子孙受累。珞元夕一生下来就遭受劫难,父死母亡,家产尽失。中原豪族的公子哥儿流落西北山村,寄人篱下,于奇门之术一窍不通,甚至大字都不识几个,原想着苦日子终有熬出头的时候,谁知再一次遭遇骁禽郎夜袭,二十多年前的一幕重演。珞元夕抱着儿子想从后门逃脱,却被埋伏在后门的骁禽郎堵个正着,折回堂屋时,被骁禽郎捅了个透心凉,草草了了此生。哎!这也是一辈子。
瘫倒在地的花氏见丈夫惨死,生怕这些人伤害自己的孩子,从丈夫手中抢过孩子,一只手拦在怀中,一只手撑地,只往后躲。这一院子的骁禽郎,她又能躲到哪里去?
花氏从苑蓉蓉处学到的那点子能耐已经技穷,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,“你们别过来!我要喊人了!你别过来!”
“哼哼!你觉得我们既来了,还会怕你喊么?”鼠长虫开口说话了,“你老老实实地交代,你男人白天拿到城里卖的金钗从何处得来,兴许我还能饶你和怀中的娃娃一命。倘若你不老实,嗯……”鼠长虫示意杀死珞元夕的骁禽郎上前抢夺孩子。
那骁禽郎附身弯腰,上手去抢花氏的孩子。还没等骁禽郎抓上襁褓,花氏从襁褓之下抽出一张黄符,正点在骁禽郎的眉心,用力往前一推。那骁禽郎冷不防这女子还敢还手,着了她的道,黄符所印之处,当场被推了出去,脑袋中间出现了一个长方形缺口。众人惊愕之际,那缺口嘭的一下,溅出鲜血和脑浆来。
花氏抱着孩子闪到一边去,躲开这些秽物,咬着牙深吸一口气,站起身来,迎着鼠长虫便跑了过去。快到鼠长虫跟前的时候,花氏又掏出一沓黄符,冲着他们来了个天女散花。吓得几人连忙往四周跳开,生怕被黄符粘上。
花氏刚才用的符纸是纸切之术,利用黄符制造出空间参差,从而达到切割的的效果。但这种高级的术,她自己不会,只是苑蓉蓉留下来的罢了。不过花氏哪来那么多纸切符呢?对着鼠长虫他们丢的只是普通的黄纸,只是鼠长虫他们没见过这种阵仗,被唬住了,给花氏让出路来。
可是幺虎是个机灵的,他敏锐地觉,花氏这次抛出的纸是空白的黄纸,来不及多想,迎着黄纸,伸手抓住了花氏的衣袖。鼠长虫和另外一名骁禽郎见幺虎没事,也立刻识破了花氏的计谋,返身回来,拦住花氏的道路。
花氏无法,只能抽出一张红符,往身后一丢。红符脱手即燃,冒出一团白烟。
三人怕这白烟有毒,忙掩住口鼻,往后倒退。
待到白烟消去,已经不见了花氏的踪影。几人忙追出门去,却看见村口也升起一团白烟,几名追过去的骁禽郎,正被呛得涕泪直流,咳嗽不已。
鼠长虫留下一名骁禽郎处理珞元夕的尸体,带着其他人追出蒲池村,捉拿花氏去了。
花氏虽然没有裹脚,但一介女流,又抱着个孩子,怎么跑得过一群训练有素的骁禽郎?
只是花氏还有苑蓉蓉留给她的三张符纸,叫月移花影,使出符纸,可以瞬间移动一些距离,只是比不过斗转星移,顶多出去一里地。这给骁禽郎的追捕着实增加了些麻烦,延长了追捕时间。直到第二天中午,花氏用光了三张月移花影。她知道这次再不能幸免,便在三叉路口最后再喂了一次孩儿,将孩儿藏在了另外一条岔路的草窠子里,自己则往通往肃南城的主路逃去。
大约过了一刻左右,骁禽郎追上花氏,将花氏掳去铁鹞子门,自此便没有了消息。
哺时二刻的时候,主路上一个三四十岁的男子挑着两筐山货,拖拖沓沓地走来了。
这个人就是亓家窝窝村的亓雄风,他满脸疲惫,神情沮丧。今天去肃南城卖山货,山货没卖出去,还倒交了摊位费,原本日子就艰难,指望着攒点山货卖,救济救济,谁知道出来这一天,反倒赔进去了,到现在一口冷饭也没吃上。也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。他走两步,就叹两口气,晃晃荡荡来到了岔路口。
这个岔路口一边往蒲池村去,一边往亓家窝窝村去,他实在走不动了,就放下扁担,在路边坐下,现在日头还早,歇一歇不耽误回家的。
亓雄风摘下头巾擦了擦脸上的汗,望着通往蒲池村的路,心中暗想“要是再不开壶,家里可要饿肚子了。实在不行啊,就叫家里的去趟娘家,她娘家的日子兴许还有富余,拆借拆借,等有了再还给他们。咱也不是有借无还的人家。”
亓雄风这样想着,他却忘了,他已经打老婆回娘家好多次了,第一次借的钱还都没还呢,怎么还能再借出钱来。
坐了一会,亓雄风觉得歇过来了,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,出“哎~~”的一声,站起身来骂了一句“日他舅地!”挑起担子来,准备往家走。
这是草窠里的珞湛生被饿醒了,也可能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惊醒了,开始啼哭。
四野荒地里,这声婴儿啼哭格外清晰,不由得亓雄风不停下脚步,侧耳倾听,“哇~哇~”湛生哭得声音更大了。亓雄风放下担子,朝着草丛中寻去。
“呀!怎地有个娃娃?”亓雄风看到湛生的时候非常惊讶。这个惊讶有点复杂。他和老婆亓颂氏结婚二十年了,一直没生孩子,对于孩子他是渴望的。但如今他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,自己两口子糊口都困难,捡这么个孩子回去拿什么养?
尽管这样想,亓雄风还是弯腰抱起了孩子,哄着他。“哎吆,好娃,不哭不哭。这是谁丢哈地,也不怕叫野狸子叼了去。”
亓雄风抱起孩子,现有些不对头了,襁褓里还缠着一个灰布包包,怪沉的。亓雄风把孩子放下,打开布包查看。他一眼就看见里面的两块金条了,“这莫是金子?听说金子一咬是有牙印的。”他将金条放在嘴里一咬,还真能咬动!他迫不及待地又咬了另外一块,也能咬动。这是该自己财!
此刻一股热血直涌脸面,他只觉得脸上热,头脑胀。迅地将布包包好,揣进怀里,就要离开。忽地他想起地上还有个孩子,迟疑了两三秒,他又回过头来,抱起孩子回到了路上。他四下瞅瞅,没有人看到。便把襁褓放在山货担子里,从山货里抽了一小节黄芪,递到湛生嘴边吸吮。湛生暂得了东西,便不再哭闹。
此处离其家窝窝村,还有七八里地,要是按之前的度,他得走到太阳下山,此时的亓雄风却如吃了老山参一般,浑身是劲,脚步轻快,酉时初刻就到了亓家窝窝村外。
老远他就瞧见自家女人坐在河边洗衣服,怕引起人的注意,亓雄风不敢高声呼喊。他摸了摸胸口的布包还在,加紧脚步往河边走去。
亓雄风的女人亓颂氏,娘家在蒲池村,嫁来亓家窝窝二十来年,一直没有生育。开始时和村里的妇人们还有交往,因为一直没有生育,逐渐地村里的妇女就有嚼舌头的,最后归结的原因是亓颂氏私德不淑,才没有孩子的。在跟说闲话的女人大打出手之后,她在亓家窝窝村的社交生活也断送了,即便出来洗衣服,她也是下午没有人的时候出来洗,不跟其他女人扎堆。
亓雄风躲在河边的芦苇丛里,压低声音喊道“家里的!家里的!”